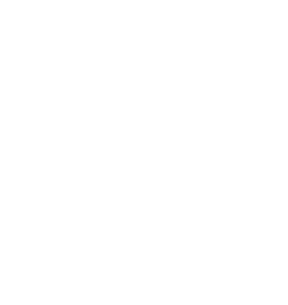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由农用土地、水资源、农业生物物种及其布局而形成的生产体系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维系粮食生产系统的多样性,稳定其结构和功能,提升其韧性。通过提高农业生态系统韧性来稳定提高粮食产能,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模式下保护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1][2]。在现代农业框架下,只有合理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才能构建稳定、可持续、健康、高产量的农业生态系统,并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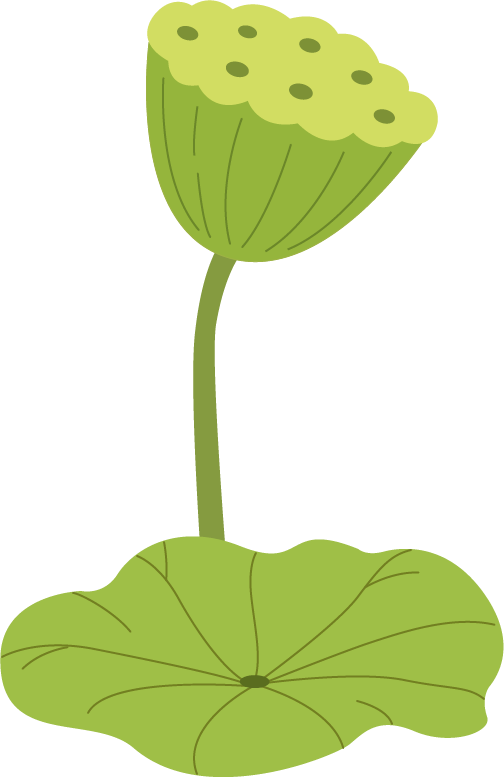
气候因子和地理因子等自然环境因素对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基础性的影响。
干旱少雨对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大,导致相关生态功能降低,作物产量下降;高温多雨、水热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会更加丰富,相应的生态功能更强;在水域充足复杂的环境中,水域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会更加丰富;在地势复杂、地形起伏大的地理环境中,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也会更加丰富。
其中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因子最为敏感,尤其是全球变暖、大气中CO2浓度的升高和降水量的变化都很可能加大农业系统的压力,加快农业产量的下降[3][4]。
农业生产方式属于人为干扰,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会加速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丧失[5]。农业生产主要包括种植制度、整地、施肥、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部分,其中种植制度又分为轮作、间作、套作和作物布局等,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影响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重要因素[6]。农业生产方式中农田的套作、轮作会改善农田生物群落多样性,从而对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提高起着直接的积极作用[7]。而不科学的耕作、不合理的施用肥料和农药则会给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带来消极的作用。
外源输入
农业生态系统属于一个半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生物与其生境相互作用并进行物质交换与能量循环,外源碳输入可能会改变参与土壤碳氮循环相关的微生物的丰度,进而影响土壤呼吸,从而影响土壤碳氮循环和农业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变化[8]。
集约型的生产方式及高产品种推广
集约型的生产方式和高产品种的推广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方式。自绿色革命之后,中国农业产量创历史新高。然而,在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单一的品种种植过分依赖少数几个作物类型,会造成毁灭性病虫害的大面积暴发。遗传多样性低、遗传背景狭窄会导致农田生物多样性降低,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因此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内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从而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抗逆性能力,从而更好地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9]。
农田景观结构
农田景观结构对农业物种多样性与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极为重要。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郊区农田景观规模不断缩减,主要被城乡建设用地侵占,农田景观向着离散化、破碎化的趋势演变,景观连通性低、生态廊道中断,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减弱,严重地破坏了大城市近郊区农田景观的稳定格局[10]。农田的种植结构组织的合理性,甚至是农田边缘的农田边界防护林结构配置的合理性,都会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和稳定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量也迅速增加。据统计,2020年截获有害生物59.08万种、检疫性有害生物6.51万种。在农田中,外来物种入侵时,当地农田生态系统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入侵物种在与当地物种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导致原有物种衰退和消失,改变了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并严重影响当地农田生态系统的各项功能,使得原本农田物种数量不断减少甚至灭绝,最终导致当地农业生态系统单一和退化[11]。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民族形成了与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相关的民族传统习惯文化。当地的农业生态系统影响着当地民族传统文化,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当地的农业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并互相影响[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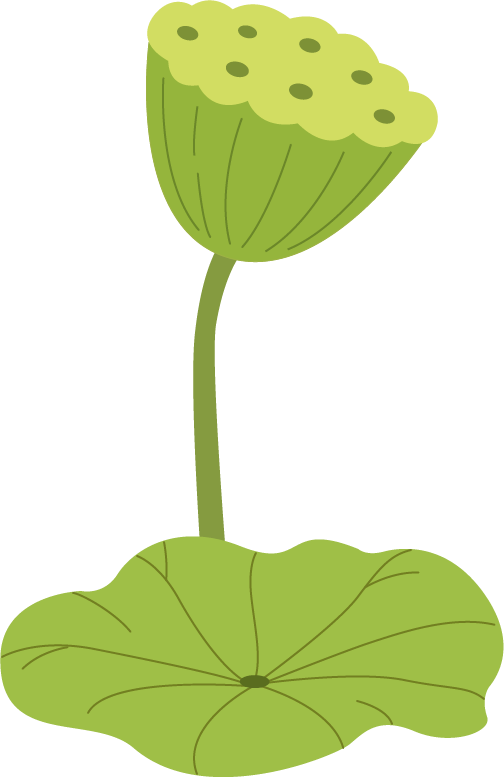
生态系统多样性概念的提出
Tansley(1935)[13]创造了“生态系统”一词。Lindeman(1942)[14]引入了现代生态系统的概念。Fisher等(1943)[15]首次提出了“多样性指数(index of diversity)”的概念。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理论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生态学家May等人提出了“农业多样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至今,涌现出了较多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研究与论述[16-18]。Altier和周锦铭(1992)[19]首次强调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应用。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评估
之前的研究只停留在简单的定义和保护措施上,随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一些表述景观多样性特征的方法也建立起来,景观生态学中分析斑块类型多样性的定义和概念也随之应用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分析。
环保意识的觉醒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自此政府开始认识到我国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1977年我国开展了环境质量普查。
认识到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性
高亮之(1980)[20]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的定义,指出农业生态系统就是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农业技术3方面组成的综合体系。闻大中(1995)[21]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定义和分类。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评价指标的建立
袁从祎(1995)[22]提出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多样性的评价体系。许健民等(1997)[23]建立了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数据库。章家恩(1999)[24]提出农业生态系统包括了产业结构、景观、物种和遗传的多样性。卢兵友和蒋广洁(2001)[25]发现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提高与结构的合理化会对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综合管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之后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种植制度、作物种类、保护管理措施等,其研究内容还扩展到了人类食品安全,同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有紧密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首次把生态系统多样性从生物多样性中提出来单独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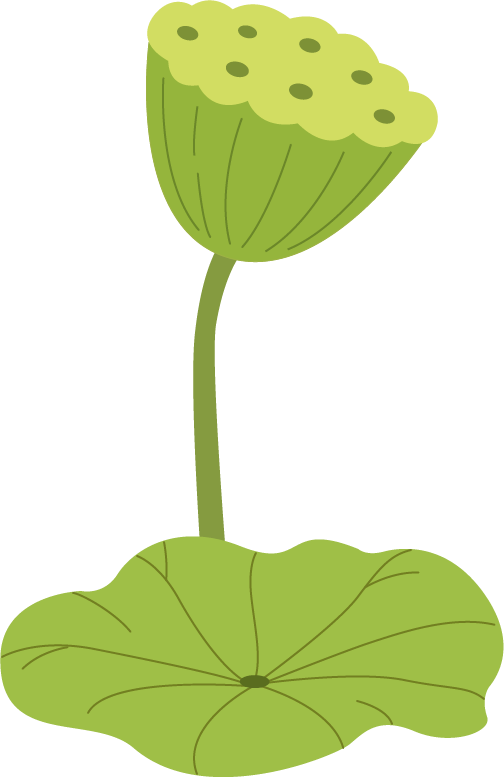
原生境保护主要是让生物继续在原始生存地栖息,并建立保护区使当地生态环境不被破坏。
国际上主要将原生境保护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物理隔离(physical isolation)方法,另一类为主流化(main streaming)方法[26]。主流化方法往往需要当地农民有很强的学习和参与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意识。
原生境保护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完整地保存物种的遗传多样性,还可以进一步使科学家在将来的研究中不断地发掘其潜在的利用价值[27][28]。原生境保护是既保护物种的遗传特性,又保护物种的遗传变异性,同时保护点建成后能够长期维持,其当地特殊的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也得以保护[29]。
异生境保护是通过建设种质资源库将其迁移到其生境之外的地方进行保护,从而避免了遇到无法抵挡的自然灾害或者人为活动时遭遇灭绝。异生境保护是对原生境保护的有力补充,只能作为一种便于研究与利用的方式。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发现,约80%种质资源已经在原产地或原生境消失,通过异生境基因库保存的资源,可以经过扩繁重新充实种质资源库,使其得以继续为当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恢复提供服务[30]。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重视种质资源的保存,至2020年底,我国已建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培育基地400多处,其中植物园和树木园近200个,保藏种质资源共105万份以上[31]。其中仅农作物就保存约50万份[32]。
通过农业生产的合理利用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方式近来也成为一大热门。如不同科属的作物进行间作或不同品种间的混播。有关研究发现,辣椒和玉米间作可以降低炭疽病的发病率,延缓病害的发生[33]。
以生态系统多样性布局为基础,将不同农作物品种进行混合栽培的科学模式,既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品种的作用,同时也避免了单一品种收益不好时而造成的颗粒无收。
农业生态景观保护的关键在于区分并优先保护农业景观生物丰富的热点区域,保护和建立连接残存的自然、半自然生境或新建生态廊道增加农田景观的连接度,提高集约化程度较低的农业用地面积[34]。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生态多样性优势、独特的农业生态景观以及优秀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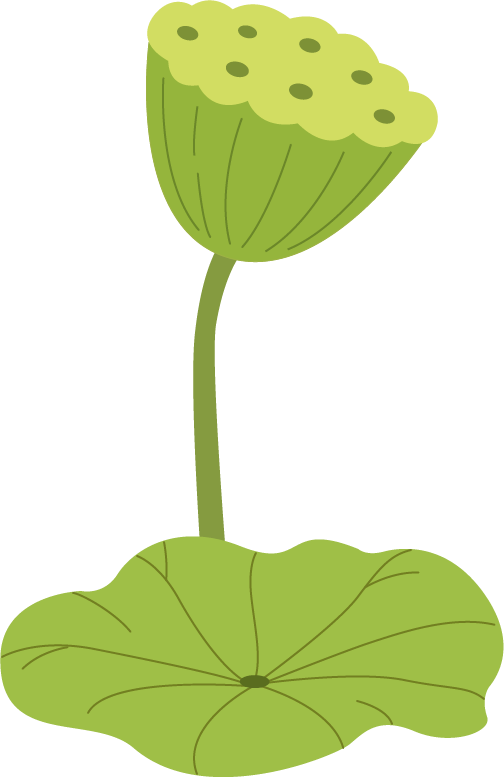
从目前的研究和保护利用情况看,今后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
完善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评估指标和方法,建立物种多样性保护基础数据库。
加强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管理政策和协调机制。
加大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力度,过度开垦及大量化肥农药投入、外来物种入侵、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主流化,重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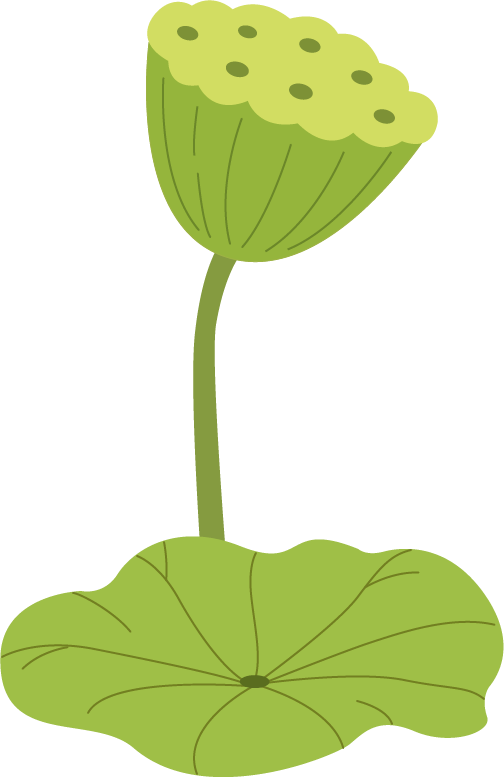
[1] Bommarco R, Kleijn D, Potts SG (2013) Ecological intensification:Harnessing ecosystem services for food security.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8, 230–238.
[2] Tscharntke T, Clough Y, Wanger TC, Jackson L, Motzke I, Perfecto I, Vandermeer J, Whitbread A (2012) Global food securit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51, 53–59.
[3] 蔡运龙 (1996) 全球气候变化下中国农业的脆弱性与适应对策. 地理学报, 51, 202–212.
[4] 肖国举, 张强, 王静 (2007) 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进展. 应用生态学报, 18, 1877–1885.
[5] 杨曙辉, 宋天庆, 陈怀军, 欧阳作富 (2010)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技术体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农业环境与发展, 27(1), 1–7.
[6] 陈欣, 唐建军, 王兆骞 (1999) 农业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 7, 75–80.
[7] 罗益镇 (1995) 生物多样性与害虫的综合防治. 世界农业, 10, 26–27.
[8] Xue K, Yuan MM, Shi ZJ, Qin YJ, Deng Y, Cheng L, Wu LY, He ZL, Van Nostrand JD, Bracho R, Natali S, Schuur EAG, Luo CW, Konstantinidis KT, Wang Q, Cole JR, Tiedje JM, Luo YQ, Zhou JZ (2016) Tundra soil carbon is vulnerable to rapid microbial decomposition under climate warming. Nature Climate Change, 6, 595–600.
[9] 唐建军, 潘晓玲 (1997) 属间远缘杂交水稻耐旱性生理特性的比较研究.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 82–86.
[10] 赵婷婷, 张凤荣, 牛振国, 姜广辉 (2009) 北京市顺义区农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8(3), 106–111.
[11] 陈兴 (2017) 外来生物入侵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危害及预防. 现代农村科技, 11, 31–32.
[12] 罗瑛 (2022) 生态民俗传承促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以兰坪县普米族田野调查为例. 文化遗产, (2), 142–150.
[13] Tansley AG (1935) 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 Ecology, 16, 284–307.
[14] Lindeman RL (1942) The trophic-dynamic aspect of ecology. Ecology, 23, 399–417.
[15] Fisher RA, Corbet AS, Williams CB (1943)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a random sample of an anim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12, 42–58
[16] De Steenhuijsen Piters B (1995) Diversity of Fields and Farmers:Explaining yield variations in northern Cameroon. PhD dissertation, Wageninge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ageningen.
[17] Collins WW, Qualset CO (1998) Biodiversity in Agroecosystems. CRC Press, Boca Raton.
[18] Brookfield H, Stocking M (1999) Agrodiversity:Definition, description and desig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9, 77–80.
[19] Altieri MA, 周锦铭 (1992) 生物多样性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应用. 资源开发与保护, 2, 158–160.
[20] 高亮之 (1980)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与我省农业现代化. 江苏农业科学, (2), 5–8.
[21] 闻大中 (1995) 试论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应用生态学报, 6, 97–103.
[22] 袁从祎 (1995)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生产力与多样性评价指标. 应用生态学报, 6, 137–142.
[23] 许健民, 闻大中, 罗良国, 罗启仕(1997) 我国主要类型农业地区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8, 37–42.
[24] 章家恩(1999) 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农村生态环境, 15(2), 36–40.
[25] 卢兵友, 蒋广洁 (2001) 村级农业生态 系统结构多样性与系统可持续性研究. 农业环境保护, 20, 145–147.
[26] 王云, 袁红娟, 许玉良, 彭友林(2013) 常德市农田野生植物资源多样性的调查. 贵州农业科学, 41(2), 33–38.
[27] Jones A, Dukes PD, Cuthbert FP (1976) Mass selection in sweet potato:Breeding for resistance to insects and diseases and for hort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101, 701–704.
[28] 陈成斌 (2002) 试论野生稻资源遗传多样性原生境保存. 植物遗传资源 科学, (3), 53–57.
[29] 杨庆文, 张万霞, 贺丹霞, 陈大洲, 戴陆元, 陈成斌, 黄坤德 (2003) 中国野生稻原生境保护方法研究.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4, 63–67.
[30] 辛霞, 尹广鹍, 何娟娟, 卢新雄 (2022) 国家作物种质库资源长期安全保存进展. 中国基础科学, 24(5), 24–29.
[31] Tucker G, McConville A, McCoy K, Brink PT (2009) Scenarios and Models for Exploring Future Trends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Changes. Final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G Environment on Contract. https://edepot.wur.nl/90914. (accessed on 2023-01-11)
[32] 周桔, 杨明, 文香英, 李楠, 任海(2021) 加强植物迁地保护, 促进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 中国科学院院刊, 36, 417–424.
[33] Gao Y, Ren C, Liu Y, Zhu J, Li B, Mu W, Liu F (2021) Pepper–maize intercropping affects the occurrence of anthracnose in hot pepper. Crop Protection, 148, 105750.
[34] 刘云慧, 常虹, 宇振荣 (2010) 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一般原则探讨.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6, 622–627.
[35] 但方, 王堃翯, 但欢, 王刚 (2022)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世界农业, (5), 108–118.

参考资料:廖美哲,张宗文,白可喻.中国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研究现状与展望[J].生物多样性,2023,31(07):166-181.
转载声明:有原创标识文章,请发送【文章名称+待授权公众号名称及ID】向我们申请白名单授权。
免责声明: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如有任何不妥之处,请联系改正或删除。